美国法院对 Uber 的宣判, 结论让国人汗颜……
在全民吐槽各大城市的网约车实施细则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来凑热闹。10月7日,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一个判决书中宣称, Uber和Lyft等平台不需要接受类似出租车的价格监管,而司机也不需要获得出租车经营牌照。 这个案件的原告是伊利诺伊运输贸易协会,它是一家由出租车公司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毫无疑问代表了出租车从业者的利益,而被告是芝加哥市政府,负责出租车的监管政策。
之所以会有这场诉讼,是因为出租车公司表示,对出租车和交通运输网络提供者(Transportation Network Providers, TNP)差别化的监管标准,是非法的且有歧视性,不利于市场竞争,使得出租车行业的利益严重受损。
利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业者的收入下降。 据悉,由于在芝加哥地区有9万名司机工作在Lyft和Uber平台上,出租车的收入下降了多达50%。 二是出租车牌照的价值贬损。 出租车公司的律师表示,由市政府发放的牌照价格于2013年创下历史最高点,即35.7万美元。然而近期,公司之间的牌照转让价格仅为6万美元。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何为交通网络运输提供者,即TNP。按照芝加哥的法规,TNP又可以称为出行共享公司,是指通过依托于互联网的平台或者数字平台来连接乘客和司机提供预约交通服务的公司。看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TNP就是指像优步、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出行平台。在美国,不同的州对优步这样提供网络预约服务的称呼并不相同,比如在加州,它们就被称之为交通运输网络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ies, TNC),不过其内涵和外延倒是大同小异,加州是这样规定的,所谓的TNC指的是通过在线App或平台连接私家车主和乘客以提供有偿预约交通服务的组织,而不管该组织的形式是公司、合伙或者个人独资等其他形式。
为什么出租车公司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竞争呢?那是因为从2014年9月2日开始,芝加哥有关TNP的监管政策开始实施,根据有关规定,TNP不需要和出租车公司一样接受价格限制和数量管制,而且允许私家车直接上路接客,只需要缴纳少量的费用就可以,芝加哥市政府要求TNP司机缴纳300美元参加在线课程学习即可。
本案的主审法官是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说到波斯纳,这也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在担任联邦第七巡回法庭法官之前,波斯纳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他是法与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尽管他现在的主业是法官,每年要审理100多个案件,但是他在工作之余还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用少量的时间写了大量的法律评论、学术论文和专著。波斯纳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皮克曾这样评价他:“ 他(波斯纳)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纪伟大的法律思想者之一。 ”因为他的渊博学识,他还在2000年以特殊的身份参加了一场备受世界瞩目的美国政府诉微软的反垄断案,而这个特殊的身份就是美国政府指定的微软垄断案调解人。

那么,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院是如何看待原告的诉由呢?波斯纳在法院判决书中首先认为TNP和出租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关于优步和巡游出租车的不同,学界和业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波斯纳认为核心点在于传统出租车客户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合同公司与司机,意即很多学者通常说的“一锤子买卖”,无法讨论价格;而TNP却通过登录的方式使得乘客与公司之间有了明确的包含保险在内的合同关系,而且在乘车前可以看到司机、车辆的照片及评分信息。所有的这些都是巡游出租车所不具备的, 决定了以优步为代表的TNP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芝加哥市政府给TNP予以巡游出租车完全不同——实际上就是更宽松的——监管也是合理的。
随之产生的就是出租车公司们认为的第二个问题,即出租车公司认为不同的监管使得其遭受了不同的竞争环境,从而导致其利益受损。因此,出租车公司援引美国宪法认为自己的财产权受到侵害。法院又是如何看待呢?
波斯纳在判决书中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TNP和出租车确实是竞争关系,而且由于TNP的出现,使得出租车的生意下滑,而且牌照也不值钱了。但是他认为, “财产”并不能具有免于竞争的权利 :
“持有咖啡厅营业牌照并不意味着牌照持有人可以阻止一家茶馆开业。尽管这一牌照允许以特定方式在市场上展开经营,但持有牌照并不意味着有权在市场上排除竞争。专利权代表的是制造及销售专利产品的独家权利,而不是阻止竞争对手发明未侵权的替代产品,防止自己的利润受到损失。实际上,当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诞生时,通常的结果是老一代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式微甚至消失。如果老一代技术或商业模式获得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新生事物排除在自己的市场之外,那么经济发展将可能停滞。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出租车,而只有马车;不会有电话,而只有电报;不会有计算机,而只有计算尺。”(此处翻译转自腾讯科技李慧,在此致谢)
出租车牌照受损是不是可以获得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意即牌照价值贬损可以视为是政府的征收进而要求补偿?波斯纳梳理了芝加哥有关出租车的管制框架后认为:
“如果一个人想无证运营出租车,这将是被禁止的,这是因为他或她违反了芝加哥市的规章,而不是因为他或她侵犯了牌照持有者的财产权……芝加哥市确实创设了出租车牌照上的财产权;它并没有在所有的机动车载客商业交通中创设财产权”。
也正是如此,波斯纳认为原告,也就是出租车公司的诉由——市政府征收了他们的财产而没有补偿金,牌照并不是宪法上保护的财产权,而且由于竞争而失去的价值贬损是不可能获得补偿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判决得到哪些启示?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像滴滴和优步这样的公司并不是出租车,因此不应该适用出租车的监管框架。尽管现在中国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一个词以示区分,但我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由此导致了事件中的种种错位。比如目前各地的实施细则中,甚至在很多地方套用出租车的监管模式——而这些问题是网约车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的问题,从而导致了监管手段和目标的不匹配,并加重了企业——间接加重了消费者的成本:比如说要求车上加GPS设备,网约车已经通过移动互联网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而所谓的“错位竞争”,要求网约车高价更在某种程度上看是为了保护出租车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设想一下,假设一项技术进步和管理革新不能让更多的民众受益而只是服务于高收入人群,这样的技术进步意义何在?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必然是价格下降,而不是相反。大卖场替代零售小店,是因为它的价格便宜;福特T型车之所以能够胜出,就是因为生产组织形式变革带来的成本下降;移动电话之所以能够进入千家万户,就是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价格下降……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政府并没有区分TNP或者TNC是否商业性营运或者是非营利性的个人合乘,都是把两者放在一个监管框架下。而中国的很多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广州还特意在关于私人合乘的意见中指出私人合乘平台必须与网约车平台区分,这实际上又是和互联网的性质相违背,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在波斯纳所撰写的这个判决书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句话:
“当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诞生时,通常的结果是老一代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式微甚至消失。 如果老一代技术或商业模式获得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新生事物排除在自己的市场之外,那么经济发展将可能停滞。 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出租车,而只有马车;不会有电话,而只有电报;不会有计算机,而只有计算尺。”
为什么美国每次都能站在技术革命的前沿?我想这是其中的要害。也希望我们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能够保护创新,而不是为了保护既得商业模式而新进入者一筹莫展。从小处说,这会让消费者利益受损;从大处来看,则会有损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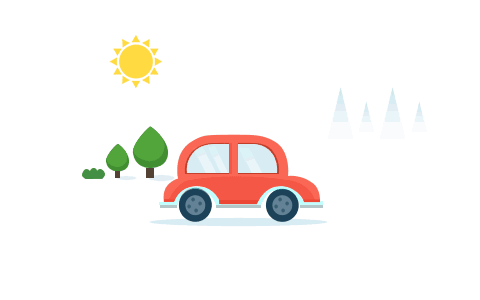
据新京报报道,就在前几天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上,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在中外创客领袖座谈会上向李克强总理反映“不要一棒子打死网约车”,而总理随即表示,会要求有关城市进行研究。我想,总理对新经济的殷切期望,会不会因为监管政策而半途而废。如果各个城市交通主管人员不了解何为网约车,不妨来看看波斯纳的这份判决书。
附:网约车司机的“乡愁”:进不了的城,回不去的村
十七年前的那个秋天,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而14岁的刘建东离开了家乡河北邢台市平乡县,乘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在通州的一个皮鞋厂开启了他的外出务工生涯。
刘建东的打工版图跨越了蒙古国、俄罗斯和非洲。他如今的身份,是北京的全职网约车司机,与他一起的还有32位平乡县的老乡。他们建了个微信群,叫“大东车队”。
他们睡觉的地方在北京南六环边,天安门城楼正南约20公里处,一个食品厂所在的“城中村”。他们都是老乡,男性,30多岁为主,老婆孩子留守家乡。他们的生活是中国1.7亿来自农村的那群人的典型写照。
他们大都是80后,早已与土地失去了联系。尽管还是农业户口,家中有几亩土地,但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回去耕种。大多数人都曾三番五次回到家乡,但呆不了多久,又选择再次进城。如此反复。
今年春节过后的100天里,刘建东的同村老乡陆续来到北京开网约车,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当时,一个月能赚一万元左右,少的也有七八千。
这份收入让他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得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司机的身份与北京建立了新的联系。但与过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亲密不同,新的联系显得有些脆弱。
网约车新政“京车京籍”的要求,给这段脆弱的关系砸了下重重一锤。上半年,“这边人多,快来拉啊”这样的信息,还在“大东车队”微信群里互相传递。随着北京网约车新政消息的发布,这个微信群如今越来越沉寂。
他们都在讨论未来要干什么,网约车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开。有人说,不给干就去开黑车。大东车队的命运就像北京不时出现的雾霾,让人看不到前方。
一
大东车队居住的地方,紧挨着南六环,附近有许多工厂厂房。没有高楼,空气偶尔飘过塑料燃烧的味道,这里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老乡们全部住在以食品厂为圆心的城中村里,其中20多人住在同一幢楼里。这是一栋4层的筒子楼,每个房间约十一二平米,一般两三个老乡睡一间,每间每月500元。
这天是星期二,中午阳光明媚刺眼,但如果不开灯,楼里就漆黑一片。一个老乡说,这里就是比较潮湿。
刘华把被子拿到楼道走廊“晒”,那里采光好些,不过依旧晒不到太阳。刘华是这群司机的介绍人,32岁,当初就是他把刘建东的同村老乡们带到了北京。
住在2楼的刘建东,1985年出生,1999年进城,十几年来做过流水线工人、建筑工、收银员以及今天的网约车司机,现在有3个儿子,媳妇在家乡带着。他在家乡还有三亩地,父母在种。
刘建东的职业经历,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切换。1999年,第二产业是中国经济的第一驱动力,占三大产业比重45.76%。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江浙地区发达的制造业,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进城务工人员,流水线上坐满了来自外省的工人。
而随着房地产在中国的兴盛,给外来务工人员打开了另一入口。2003年8月份,国务院发文将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不断增加,楼盘在一座座城市里拔地而起,建筑工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里。
服务业则在2014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且互联网经济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快递员、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成为打工者们最新的阵地。伴随着产业的兴替过程,这群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刘建东说,他们这一代人,基本没人再愿意种地。过去,种庄稼带来的收入可以养活家里几口人,再换些钱过生活,基本够用;如今,种庄稼的收入,一亩地能赚几百元就已经算不错。
他掰着手指头仔细算了一下账,按照今年的玉米价格,除去肥料、除草和收割等成本,基本只能刚回成本。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每亩地一年是100多元。
刘建东说,如果种地能够解决家庭温饱,够小孩的学费,谁不愿意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因为不挣钱,所以把人赶进了城市。“就算回去了,也还是得出来,因为没钱挣。”刘建东过去已经回了家乡好多次,最后仍然跑了出来。
“而且物价涨得太厉害,”刘建东说,现在的钱不像过去“经得起使”,他的大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每年学费生活费要2万元,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念一年级和幼儿园,开销也不小,种地的钱,根本不够用。
与刘建东相比,1994年出生的王果智,从来没种过地。王果智家里有六亩地,他说估计一亩地一年应该能挣个一千来块钱,一旁的刘建东听了立刻叫了起来:“哪有一千来块钱!”
王果智声音减弱了几分:“啊,没有吗?”他是大东车队里面年龄最小的,有三个姐姐。
2010年,初中没毕业的王果智想到外面看看世界,跟着几个同乡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当时月薪1500元。后来的几年里,陆续回家了几趟,又多次进京,相继做过网管、保安队长、电工和司机。
王果智说,感觉以前人都特别重视土地,但是现在都不怎么重视了,“随它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过,刘建东说,家里的地哪怕不挣钱,也不能让它空着,“空着会遭村里人笑话”。
如今,不论是80后的刘建东,还是90后的王果智,离祖辈们曾赖以生存的土地正越来越远。对他们来说,更为熟悉的生活方式是在城市里游走,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如果不挣钱了,就再换一份。
二
王果智已经不再像刚来北京的时候一样,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忍受低廉的工资。23岁的他,开始把结婚的事情提上日程,并且在家乡相了好几回亲。
王果智说,在他们家乡,男方有房有车的前提下,需要给女方10万出头的彩礼钱。他们90后这一代正碰上计划生育抓得紧,很多人怀孕的时候都去查性别,只想要个男孩,导致当地男多女少。
这让娶媳妇的事变得更加困难,女方对男方的经济条件要求越来越高。王果智把挣钱作为找工作的第一目标。而对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大东车队大多数80后来说,这一目标从未改变。
像刘建东这样30多岁,结了婚,有老婆和要上学的孩子的,是车队里的典型。他们有的是以每月4000元到5000元的价格租的车,有的车是老乡贷款自己买的,价格在8万元到10万元之间。租来的车自带北京牌照和保险,买车的老乡则需要另外租一个北京牌照,每年13000元,然后再付一年4000多元的保险费。
绝大多数人把老婆和孩子留在家乡,28岁的赵农是为数不多的带媳妇一起来北京的人。他今年七八月份贷款买了车,10万元的大众朗逸,贷款五六万,现在每个月还5400元,要还满一年。
房间里,赵农边用手机开着直播。他说,这个直播开上一天,可以拿100元左右的补贴,“什么都不用做,打开放着就行。”
赵农说,直播的补贴肯定也会慢慢没有的,就跟那些网约车的补贴一样。当初开网约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能补贴会消失?问题一抛出来,旁边的刘华抢过话头说,没想到会这么快,原以为补贴起码会持续个一年半载,没想到几个月就“噌噌噌”往下降。
网约车新政的消息传开之前,他们每天开车的时间都在十三四个小时。刘建东说,因为车子投入太大,几乎每天的前十个小时都是在为贷款、保险和油费开车,后面的三四个小时挣的钱才是自己的。
几乎每个人都会尽量多开一些时间。早上7点起床,晚上12点回家,是他们工作的常态。车辆限行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休息日。
喜不喜欢北京?刘建东说:“喜欢啥啊喜欢,还不是为了挣一两个钱。”从开车至今的大半年时间里,他拉过上千个乘客。刘建东至今没交到一个北京本地的朋友。在他眼里,北京人吃喝不愁,买车有车补,加油有油补,而他们只有种地的补助。
空闲的时候,刘建东和老乡们也几乎不怎么去北京别的地方,开车几乎是他们与北京唯一的联系。一天十三四个小时驾驶时间下来,他们疲惫不堪,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而他们觉得自己早已经过了出去玩的年龄,身上负担太重。“北京,钱比老家好挣啊,”刘建东说:“你出门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挣钱,要是不挣钱,还不如呆在家里。”好几个老乡说,幸苦不怕,能赚到钱就行。
三
现在,这份唯一的联系也在风雨中摇摆不定。刘华说,新政出来后,大家都很心慌。之前,他每天早上7点出门开车,车子每天洗、天天擦。现在,心情好就去拉一拉,有时候睡到10点才起床,一点动力都没有。中午见到老乡齐士辉的时候,刘华正躺在床上用手机看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一个网约车新政研讨会上的发言。
沈岿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目前以北京市网约车征求意见稿的细则来看,它跟五个原则可能会存在抵触或者不一致的情况……”齐士辉盯着手机屏幕说,有人替他们司机说话了,觉得至少有个心理安慰,会舒服一些。
法律专家的话有没有用,政策会不会改变?他心里没底。
心里没底的不仅仅是齐士辉。如今,大东车队的微信群越来越沉寂,开始陆续有人另谋出路。已经有人找了快递员的工作,也有人想把刚买几个月的车卖掉,更多的老乡还在观望中,一边找新的工作,一边时不时出去拉几单。
开车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是被“钓鱼执法”。跟齐士辉一起住的郭房说,自己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一个地方开滴滴的时候,被钓鱼执法,罚了3000元。为了证明此言不虚,他把收据的图片拿了出来。
但网约车司机是他们的理想职业吗?刘建东和齐士辉自言自语地重复了几声:“理想职业……理想……”然后说:“嗨!没啥理想,关键是能挣钱就行。”
刘建东反问:“衣食无忧了才能谈理想,没吃没喝啥都谈不成,对不对?”
刘建东和齐士辉对未来并没有什么计划。但他们的共识就是,现在不能回农村,农村不挣钱,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必须留在城里才有机会。
中国的城市正越变越大,但对城镇化来说,这还不够。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城市的常住人口计算在内,这意味着只要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便被统计在内。大东车队的老乡们,或许都曾被算作为城镇人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城里人。户籍制度目前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从教育、就业、医疗到养老,户籍几乎贯穿每一个普通人一生所有的重大环节。若以户籍计算,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而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齐士辉是车队里为数不多的接触过社保的人,他之前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时候,工厂给他买过一段时间的社保。然而,刘建东和王果智却搞不清楚“五险一金”区别在哪里,他们想了一会,说出了住房公积金和医疗、养老保险。然后王果智说,这东西感觉对他没什么用。或许齐士辉也有理想,那就是成为北京人。他对刘建东说,下辈子做北京人吧,出生了身家就是几百万以上——这的确是一些外乡人对北京的看法,虽然用来形容所有北京人并不公道。不过,刘华觉得最悲哀的是,如果可以继续开网约车,还能慢慢想办法提高收入,但现在,关键是不让外地人干,“就一点希望没有了”。
文/我是栗子姐
关键字:产品经理, 网约车
版权声明
本文来自互联网用户投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如若内容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事实不符,请点击 举报 进行投诉反馈!
